杨 宗 泽
在世界当代诗坛上,有一颗异彩亮丽的星辰,这颗星辰就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是彝族,是这个以鹰为图腾的山地民族的优秀儿子,是翱翔在人类诗之苍穹的一只雄鹰。他的诗有“太阳的光辉”,也有“森林的颜色”;他的诗蕴藏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梦,这个梦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对于彝族这个古老民族而言,吉狄马加是一个符号,一个具有诗歌精神和民族精神双重内涵的文化符号。他的诗不但使一种古老文明得以延续,而且赋予这种文明以鲜活的时代气息;他的诗以深邃而精妙的意象组合、形神合一的诗美特质和明畅的叙事风格语句将彝族的历史、文化、神话、习俗以及这个民族目前的生存状态呈现给世界,使人们领略到这个古老民族的楚楚风采,触摸到这个民族以“红、黄、黑”三种颜色为情感基地的内心世界,并在当下多元并存的诗歌格局里找了属于诗人自己的位置,显示了一位诗坛大家在文化心理方面的睿智与艺术追索方面的高踔。
吉狄马加的诗具有深刻的民族性,跃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充满了诗人对于他的民族和养育他的那片土地以及繁衍生息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源于血脉的挚爱。他的诗大都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命运和未来等人文角度入笔,侧重于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心理的打探,在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抵达了一般诗笔所难以与之比肩的艺术境界。吉狄马加在文化视野和诗美空间的拓展方面显示了他独特的审美体悟与审美个性,并以此为契机,写出了颇具史诗韵味的当代彝族诗歌的最新文本,从而使彝族当代诗歌站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当代诗歌的前沿。
从吉狄马加的诗里,我们可以品味出一种乡愁情结,这种乡愁情结是诗人心底里的民族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诗人民族文化忧患心态的折射,具有文化乡愁的特征。这种乡愁情结象一段歌谣,其古老而神秘的旋律恰如诗人在《部落的节奏》一诗里所说的,即使“在充满宁静的时刻 / 我也能察觉到 / 它掀起的欲望 / 爬满我的灵魂 / 引来一阵阵风暴”,甚至在梦乡里,“我也能发现 / 它牵出的思念 / 萦绕在我的大脑 ”。对于吉狄马加来说,这种文化乡愁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富于使命感的神圣力量,而且,多少年来,诗人就是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在“淡淡的忧郁中”写出了那么多“关于彝人的诗行”。吉狄马加诗歌里所传达的这种文化乡愁不仅是诗人对于包括自身艺术生命在内的个体命运的思考,更多的却是诗人对于日益严重的世界性文化同化给文化个性带来的扼杀的反抗与愤懑,也是对于一个民族的命运和未来深具忧患色彩的担忧,恰如印在《吉狄马加诗选》封底的那段文字所言,“毋庸讳言,对于我的部落和那长长的家谱来说,我将承担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明白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我承认我的整个创作,都来自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由此可见,吉狄马加是在用诗歌承托起对于一个民族的使命,用诗歌代表一个民族发言,所以,他的诗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身份,起到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用。
吉狄马加的诗浸润着浓郁的人类情结、博爱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诗人对于人类命运的人文关怀。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诗人写于2005年的一首名叫《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诗。众所周知,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尽管法西斯早已成为历史,但在这颗星球上,枪炮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局部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人类的和平事业依旧任重道远。于是,诗人借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公交车里的一次爆炸事件为契机,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抒发了诗人对于战争和流血冲突的愤慨以及对于和平的向往。在该诗的最后一节里,诗人写到,“我不知道 / 耶路撒冷的圣书 / 最后写的是什么? / 但我却知道 / 耶路撒冷这座古城 /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 只有一条道路是唯一的选择 / ——那就是和平!”这首略带宗教批判色彩的诗作不仅是诗人对于中东和平和世界和平的渴望,也是诗人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发出的呼吁与呐喊!写到这里,我不觉油然想起吉狄马加在谈及他的诗歌创作时所说的一句话“我写诗,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核原子的时代,我们更加渴望的是人类和平。”这就是吉狄马加,一个热爱全人类、热爱和平并注重用诗歌与世界对话的中国诗人,一位具有博爱思想和人类意识、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和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光芒的中国诗人!
吉狄马加的诗是彝文化和汉文化共同培育的一朵艺术奇葩,她既蕴含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又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诗充满了诗人对于自己的民族深厚的民族情感,又透射着诗人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赤子之爱。读他的诗,你会感觉到一种震撼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诗人博大的胸怀与良知,也来自他的作品的不同凡响的艺术感染力。吉狄马加在二十多岁时,就有诗集《初恋的歌》出版,迄今已有《一个彝人的梦想》、《被埋葬的词》、《吉狄马加诗选》等10余部诗集用汉语、英语以及其它语种在国内外出版。他的诗不仅在中国当代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诗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诗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一个民族,诚如诗人在《致自己》一诗中所写的“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 / 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
(该文系应塞尔维亚国的一位研究吉狄马加诗歌的汉学家之约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写成,并选入2006年9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狄马加诗选《时间》(汉英对照)一书里。)
【读诗随笔】 民族意识与回归情结的诗性宣泄
文/ 杨 宗 泽
自2002年9月以来,受国内外几家出版社和欧**家几位汉学家的委托,我已陆续将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80余首诗作翻译成英文。我所翻译的这些诗作,有的已经用汉英对照方式结集出版,如2003年8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的《吉狄马加短诗选》,有的正在筹划出版中,有的则作为参考文本供国外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们研究、译介吉狄马加诗歌艺术之用。众所周知,在文学翻译领域,诗歌翻译尤其是将汉语诗歌翻译成英、法、德、俄等文字的诗歌也许是最难的了,因为诗歌翻译不仅是文字和语言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情感、智慧和意象的转换或再造。所以,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对原文一读再读,直到读出它的精髓和神韵来,才敢下笔开译;由是, 我敢说,在吉狄马加诗歌的读者群里,我应算是最认真的读者之一。因之,这篇文字就权作一位忠实读者对吉狄马加诗歌的一点读后感悟吧。
读吉狄马加的诗,你会感觉到一种震慑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浸润在作品里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浓郁的回归情结。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的综合体现,是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意识在诗人身上的反应往往比较敏感,这种敏感是通过他的作品来体现的。吉狄马加是彝族,是这个山地民族的一只雄鹰,一只翱翔在中国和世界当代诗坛的雄鹰。他的诗有“太阳的光泽”,也有“森林的颜色”,他的诗里蕴藏着一个梦,一个古老而神圣的梦,这个梦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所以,在《彝人之歌》里,诗人写到,“我曾一千次 / 守望过天空 / 那是因为我在期盼 / 民族的未来 / 我曾一千次 / 守望过群山 / 那是因为我还保存着 / 我无法忘记的爱”。
吉狄马加的诗作几乎处处都跃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他生命与情感的重要部分,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吉狄马加的这种民族意识是通过抒发乡情、乡音来宣泄的,但他的诗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乡土诗或乡情诗。一般意义的乡土诗、乡情诗,多是抒发作者对于家乡故土的怀念与热爱之情,且审美取向多又停留在诸如,“袅袅炊烟”、“哗啦啦流淌的小河”、“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村口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童年的小伙伴”乃至于“可爱的小花狗”与“故乡的那位望穿秋水般盼望着我归来的姑娘”等具象上,而吉狄马加的诗却总是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等人文角度入笔,并将之与故土的山山水水以及繁衍生息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与他们的命运揉为一体,宣泄了诗人对于自己的民族和故土的缘于血脉的深情挚爱以及不同凡响的、颇具文化品位的忧患心绪。读后,让你觉得深沉厚重,让你的灵魂随着作品所透射的历史沧桑感而震颤不已。《土地》一诗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 不只因为我们在这土地生 / 不只因为我们在这土地死 / 不只因为有那么多古老的家谱 / 我们见过面和没有见过面的亲人 / 都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又一个的逝去 / 不只因为在这土地上 / 有着我们千百条深沉的野性的河流 / 祖先的血液在日日夜夜地流淌 // 我深深地受着这片土地 / 不只因为那些如梦的古歌 / 在人们的心里是那样的悲凉 / 不只因为在这土地上 / 妈妈的抚摸是格外的慈祥 / 不只因为在这土地上 / 有着我们温暖的瓦板屋 / 千百年来为我们纺着线的 / 是那些坐在低矮的木门前 / 死去了的和至今还活着的祖母 / 不只因为在这土地上 / 我们的古磨还在黄昏时分歌唱 / 那金黄的醉人的温馨 / 流进了每一个女人黝黑的乳房 //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 还因为它本身就是那样的平平常常 / 无论我怎样地含着泪对它歌唱 / 它都沉默得像一块岩石一声不响 / 只有在我悲哀和痛苦的时候 / 当我在这土地的某一个地方躺着 / 我就会感到土地——这彝人的父亲 / 在把一个沉重的摇篮轻轻地摇晃”。 仔细品味一下,该诗不仅是诗人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心声的诗化呐喊。
在吉狄马加的不少诗作里,我们还可以品味出一种浓浓的乡愁情结,这种乡愁情结属于蕴藏在诗人心底里的民族意识的一部分,是诗人民族文化心态的折射,具有文化乡愁的特征。这种乡愁情结象一段歌谣,其古老而神秘的旋律,恰如诗人在《部落的节奏》里所说的,即使“在充满宁静的时刻 / 我也能察觉到 / 它掀起的欲望 / 爬满我的灵魂 / 引来一阵阵风暴”,甚至在诗人甜蜜地沉睡之时,“我也能发现 / 它牵出的思念 / 萦绕在我的大脑”。对于吉狄马加来说,这种文化乡愁情结也是一种力量,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且,多少年来,就是在这种神奇的力量的驱使下,诗人“在淡淡的忧郁中”写下了那么多“关于彝人的诗行”。那么,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文化乡愁情结是从哪些方面体现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从诗人对民族命运和民族个性的关切两个方面体现的。在《古里拉达的岩羊》一诗里,诗人以岩羊为意象嫁接,抒发了他对于自己的民族的命运的关切之情 ------“雄性的弯角 / 装饰着远去的云雾 ”而其背后却是“黑色的深渊”。岩羊是善良的,但也是无畏的,在吉狄马加的诗里,它分明就是一个山地民族的个性、品格与命运的象征。另外,在《岩石》里,诗人写道,“我看见过许多没有生命的物体 / 它们有着彝人的脸形 /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沉默 / 它们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在这首诗里,诗人以岩石、脸形与彝族人民刚毅不屈的精神品格为意象组合,抒发了诗人带有民族情感的一腔乡愁情结,确是神来之笔。在这个方面,《被埋葬的词》也许最有典型性,“我要寻找 / 被埋葬的词 / 你们知道 / 它是母腹的水 / 黑暗中闪光的鱼类 // 我要寻找的词 / 是夜空宝石般的星星 / 在它的身后 / 占卜者的双眸 / 含有飞鸟的影子 // 我要寻找的词 / 是祭师梦幻的火 / 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 / 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 // 我要寻找 / 被埋葬的词 / 它是一个山地民族 / 通过母语, 传授给子孙的 / 那些隐秘的符号”。可以说,该诗更为深刻地宣泄了翻腾在诗人心底里的那股“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般的文化乡愁情结。吉狄马加诗歌里所传达的这种文化乡愁不仅是诗人对于包括自身艺术生命在内的个体命运的思考,更多的却是诗人对于日益严重的世界性文化同化对于文化个性带来的扼杀的反抗,是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深具文化意蕴和忧患色彩的担忧,读来,让人感怀多多。
吉狄马加的这种文化乡愁心态的形成缘于现代工业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对于人类灵魂和精神家园的压抑。毋须讳言,现代工业文明尤其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是以牺牲农耕文明和自然生态为前提的,它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原生态般的亲近无疑是一种扼杀,同时,它对于民族文化和文化个性也是一种水淹孤岛般的消解与“摧毁”。在吉狄马加的诗里,我们可以明晰地感受得到。此外,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回归情结在他的诗里星星般闪烁。在《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里,诗人如是说,“怜悯你 / 就是怜悯我们自己 / 就是怜悯我们共同的痛苦和悲伤”,因为“有人看见我们骑着马 / 消失在所谓的城市文明里”。所以,当诗人面对故土的大山时,他才会感受到“那是自由的灵魂 / 彝人的护身符 / 躺在它的怀中 / 可以梦见黄昏的星辰 / 淡忘钢铁的声音”。在《追念》一诗里,诗人象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他说,“我站在这里 / 站在钢筋和水泥的阴影里 / 我被分割成两半 // 我站在这里 / 站在红灯和绿灯的街上 / 再也无法排解心中的迷惘 / 妈妈,你能告诉我?/ 我失去的口弦是否还能找到”。此时的诗人正象他在诗里所写到的,“我象一个孩子站在山冈上 / 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 / 充满忧伤”。正是因为这种深沉的文化乡愁心态的驱使,即使当诗人行走在现代城市的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的时候,他也近乎痴狂地感觉到,“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 有人在写我的名字”、“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 有人在等待我”(《看不见的人》)。毫无疑问,这个“看不见的人”就是吉狄马加的故土!就是吉狄马加所属的那个民族!因之,诗人近乎失声地祈求 ----- “让我成为空气,成为阳光 / 成为岩石 成为水银 成为女贞子 / 让我成为铁,成为铜 / 成为云母 ,成为石棉 ,成为磷火 / ……让我成为草原,成为牛羊 / 成为獐子,成为云雀 ,成为细鳞鱼 / 让我成为火镰,成为马鞍 / 成为口弦,成为马布,成为卡谢着尔*”。可以说,吉狄马加的回归情结源于他心底的文化乡愁意识。正是因了这种文化乡愁心态所衍生的回归意识的驱使,诗人在《远山》一诗里才近乎失声地呐喊,“我想听见吉勒布特的高腔 / 妈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身旁”,诗人才“归心似箭”般地“我要横穿十字路口 / 我要越过密集的红灯 ”、“我要跳过无数的砖墙”、“我要击碎那些阻挡我的玻璃门窗”、甚至“我要用头撞击那些钢筋水泥的高层建筑”,以便“选择一条最近的道路”回到那片“多情而沉睡的土地”。从以上这些脍炙人口、震撼心灵的诗句里,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位山地民族的优秀儿子对自己的故土和民族的无限怀念与热爱,感受到一位民族诗人对于现代工业文明尤其是现代城市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厌倦与对抗。
雨果曾说过,“诗人本来就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十八世纪德国著名进步文学理论家约翰.高特夫里特 . 赫尔德也曾说过,“民族的感情将会造就诗人。”我想,以上这两句名言不正是对于吉狄马加诗歌艺术追索与成就的概括吗!吉狄马加的诗,情感丰沛,语句凝重,意象鲜活而深邈,且在文化视野的开拓与民族精神的挖掘方面有其独特的审美体悟和诗美个性,已蔚成大家气度。吉狄马加刚刚人到中年,在他二十多岁时就有诗集出版,迄今已有近十部诗集在国内外用多种文字出版,其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在国内外当代诗坛都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诗饱含着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的深情挚爱,透射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浓郁的回归情结,有着民族代言人的作用。他在诗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一个民族,诚如他在《致自己》一诗中所说的“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 / 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
读吉狄马加的诗,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而且是对于灵魂的一种震撼。倘若诗人在诗歌的情绪调动方面“更上一层楼”的话,他的诗一定会站的更高,飞得更远;因之,我由衷地期待吉狄马加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了他的民族,为了我们共同的中华民族,也为了属于全人类的诗歌。
* 口弦,马布、卡谢着尔 ------- 均为彝族的原始乐器。
--------- 写于2006年元月8日
【诗人简介】吉狄马加 (1961 ----- ): 彝族,中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著名诗人、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2006年7月调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现任青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2007年8月创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担任诗歌节组委会主席。其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并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蒙古文等十多种文字发表;迄今已有《一个彝人的梦想》、《被埋葬的词》、《吉狄马加诗选》等十余本诗集在国内外以多种文字出版。
杨 宗 泽 (1953 — ) 笔名: 瘦 路;山东平度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文系,中学高级教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83年始,已有2000余件诗歌、散文、文学评论以及当代中外诗歌英汉互译作品在国内外80余家报刊发表,作品入选80多种选集或选本,数十首诗作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希腊语、日语、葡萄牙语、蒙古语等十几个语种在国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得奖项,个人艺术简历入编《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典籍。1999年12月被**世界作家艺术家协会评选为1999年度最佳翻译家。已有诗集《浪漫季节》、《无雪的冬天》和诗歌翻译集《贺敬之短诗选》、《吉狄马加诗选》、《伊曼纽尔 . 马休诗选》等28部著作在国内外出版。
欢迎点击进入
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zxhy/member/6142.shtml
中国诗歌网http://www.yzs.com/html/yangzz/yangzz.html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http://www.cbi.gov.cn/wisework/content/cn_6444.html
http://www.cbi.gov.cn/wisework/content/6444.html
**华文网站“文心社”http://wenxinshe.landaishu.com/home/blog.asp?id=2102
诗家园http://www.sjycn.cn/listarticle_268577_1268780.shtml
个人博客http://zongzeyangcn.blog.163.co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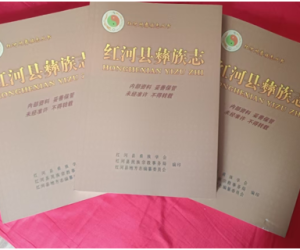 “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 《红河县彝14 人气# 彝学动态
“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 《红河县彝14 人气# 彝学动态 乌蒙村秀:千年彝裳绣出彝族文化指尖记忆25 人气#行摄彝乡
乌蒙村秀:千年彝裳绣出彝族文化指尖记忆25 人气#行摄彝乡 恳合呗:延续千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6 人气#历史文化
恳合呗:延续千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6 人气#历史文化 学彝文:每日一句谚语굈갱광꽄굈눔125 人气# 语言文字
学彝文:每日一句谚语굈갱광꽄굈눔125 人气# 语言文字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