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诗歌的民族性特征研究
文/阿侯索格
摘要:彝族是用诗思维和创作的民族,彝族诗歌是彝族文学的特殊表现形式,它的起源和发展都贯穿于整个彝族社会生活之中。彝族诗歌类型多样,体例独特,其中以五言三段诗最具民族特征。其艺术特征更能体现彝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以诗论诗”的诗论形式更是区别于其他民族诗论的重要特点,对彝族社会的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彝族 诗歌 民族性 五言 三段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先民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还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彝族文化,这些文化是彝族人民的灵魂,集中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精神面貌,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气质,心理状态。并通过文化,培养了民族性格,塑造了民族形象。
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和创作的民族,彝族传统文学,不管是书面文学还是口头文学,几乎都是用诗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整个彝族传统文学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彝族诗歌文学。诗歌作为彝族文化的精华,由于受民族居住地域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在彝族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彝族诗歌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它是指彝族传统诗歌,即古代用彝文写成的诗歌和民间用彝语吟唱的歌谣,以及近现代彝族诗人用彝汉文写成但格式和韵律都严格遵守传统诗歌风格的一种诗体。这种诗体最能体现彝族风格,因此,下面从几方面对其民族性特征作一些试探。
一、 彝族诗歌的起源
讨论彝族诗歌,就必须对彝族诗歌的起源有所认识和有所了解。
彝族是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彝族先民创作了浩如烟海的彝文典籍。如反映彝族哲学思想的《宇宙人文论》,记述彝族历史沿革的《彝族源流》,号称彝族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记录彝族原始神话故事的《彝族古歌》《物始纪略》《洪水记》,记述彝族君长大姓谱系的《彝族创始志》,阐述彝族教育思想的《码牧特衣》,创世英雄史诗《阿细的先基》《梅葛》《查姆》《勒俄特衣》《支嘎阿鲁王》,抒情长诗《阿诗玛》《妈妈的女儿》《漏卧鲁沟的婚礼》;研究彝族诗歌理论的《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彝诗九体论》等等,以及民间所唱的歌谣,都无一不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的。由此可以看到,诗学贯穿于整个彝族社会生活之中,用诗思维和创作成了彝族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那么,如何来探讨彝族诗歌的起源呢?
《彝族创世志.艺文志》记载:“天地繁花开,典章写下来,从前人说的,传远古文化,如苍茫大海,创三张华章,史事分而合,文理自然传”(1)“气清苍穹美,天地繁花开,典章写下来,议事有五章,哎哺所珍藏”.(2。“哎哺”时代在彝族典籍中是属于传说中的天和地产生的时代,应该当属原始社会。既然说“华章”为“哎哺”所珍藏,那么,至少在“哎哺”时代“华章”就已存在。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那么,劳动也必然创造了作为人类艺术的诗歌。鲁迅先生也说文学起源于人类劳动中的“杭育杭育”(4),彝族诗歌作为整个人类文学中的一部分,也必然遵循这一客观规律。脱离了人和人的劳动,诗歌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例如情歌和酒礼歌。因此,贵州彝族诗论家奥吉戈卡(王明贵)在其《彝族三段诗研究》中把彝族诗歌的起源概括为“彝族诗歌起源于原始社会,产生于劳动之中,来源于人民群众”(5)。他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来概括彝族诗歌起源的本质,符合人类艺术起源的的普遍规律。
但是,彝族诗歌的起源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宗教。作为记录彝族诗歌的彝文多是掌握在彝族布摩(毕摩)(6)手里,至今发现的几乎所有彝文典籍都是布摩(毕摩)所创,而这些典籍大多是作为祭祀的经书来吟唱的。布摩(毕摩)运用这些经书来完成他的宗教职能,经过一代代的整理修订,从而形成一部部宏大的诗歌典籍。笔者常在家乡听到布摩(毕摩)给死者念的经文,如果抛开宗教因素而论,无一不是一首精美的诗歌。因此,彝族诗歌的起源是和宗教分不开的。
二、 彝族诗歌的发展
彝族诗歌产生后,同其他民族的诗歌发展历程一样,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先是口耳相传,文字产生后便用文字来表现,继而注重形式与格律。漏侯布哲在《谈诗说文》中说:“古时的古事,先是用口传,再用文字写”(7),“写法是这样,一不讲声韵,二不讲押扣,左和右之间,他们也不押,上和下之间,他们也不连,所以那种诗,虽写难下传”(8),后来是“举奢哲大师,他们和阿买妮,他们两先哲,来整理诗文,来整理经书”(9)。虽然举奢哲和阿买妮在彝族诗歌的创作 整理和传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没有定出严格的体例。因此,漏侯布哲说“所以我现在,既要讲文论,又要讲诗律,各式各样体,各式各样题,都要试谈谈,都要试论论”(10)。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不断革新,才使彝族诗歌得到广泛的普及和流传,同时在流传中不断创新,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风格,也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诗学理论基础,构成了彝族诗歌的完整理论体系。据载,举奢哲和阿买妮是南北朝人,从他们的一系列诗歌著作和诗论著作中可以看出彝族诗歌在南北朝时已达到高度的繁荣,并且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其后一直稳定地发展至今。
三 、彝族诗歌的分类
彝族诗歌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按传承方式可分为书面体和歌谣体。书面体有叙事长诗,有抒情短诗,有诗论等,全都遵循规范的彝诗格律。歌谣体大致可分为情歌系列,酒礼歌系列,丧礼歌系列,以及用说的“克哲”(谚语)部分。彝诗歌谣体虽然是用的唱的形式来表现,但却严格遵守彝诗格律。并且每一部分都有特定的场合,相互之间不能逾越。例如情歌只能在野外唱,且多在喜庆节日如火把节等传统节日期间唱,它所唱的内容多是传达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同时,长的每一部分都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和礼仪,有专门的人员来指挥和负责,在整个婚丧嫁娶喜庆节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能体现出彝族独特的民族风情,至今在乌蒙彝区仍然广泛活跃,其旺盛的生命力仍旧生生不息。
四、 彝族诗歌的体例
彝族文化的完整性决定了彝族诗歌的独特性,也为彝族诗歌的独立发展孕育了条件,从而使彝族诗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诗歌的自身独特的体例,即五言三段诗。五言三段诗是彝族诗歌的主流,是彝族诗歌最具有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在整个彝族文学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试从“五言”与“三段”这两方面来对彝族诗歌的民族性进行分析。
(一)、以五言为主体
纵观彝族文献典籍和民间歌谣,几乎全是五言诗体的形式。虽然也有一小部分其他言的诗体,但在彝诗中的比例还不及十分之一。五言诗虽然不是彝族诗歌的唯一形式,但却是彝族诗歌的主流。那么,为何五言诗会成为彝族诗歌的一种普遍的表达形式呢?
首先,从彝族五行学说和五色观上来看。五行学说和五色观是彝族先民对宇宙天文的哲学观点,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反映在诗歌中,无疑成了五言诗句式的文化哲学背景。贵州彝族作家熊正国的民间故事《竹的儿子》记载:从竹子里生出来的五个儿子成为了彝族青 红 黑 黄 白五支系,这从一方面反映了彝族五行学说和五色观学说,也可从侧面佐证彝族五言诗的哲学基础。
其次,从彝族的语言发音来看。彝族诗歌几乎都可以用来吟唱,因此,它必须有一定的音韵美。既然要求有一定的音韵美,先民就必须采用一种便于发音且唱来动听的形式作为体例。而彝语的发音一般在五个音节之间最为协调,所以,他们必然选择了五言诗体的形式,把它规定为一种体例。布麦阿钮在《论彝诗体例》中说:“五言诗当中,五音三字合,五音三两合,五音三不合。五言诗当中,五声三音合,五声三不合,五声五相合,五声三声合,五声三不合,声韵性中分”(11),他的观点说的就是彝语语音的发音。笔者常在家乡听到的彝歌,无论经文 丧歌,还是情歌 酒礼歌,音韵都十分和谐,悦耳动听,而他们却无一不是五言诗。
五言诗是彝族诗歌的主流,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由此也产生了彝族独特的五言诗论,这些诗论同样也是一首首精美的五言诗。从而使彝族古代的诗论也作为五言诗的一部分而存在,大大拓宽了五言诗的范围,增强了彝族五言诗的社会理论基础。
(二)、以三段为精华
王明贵说彝族古代文学的精华部分是三段诗,的确,在所有彝族古代文人创作的诗歌和民间歌谣中,几乎都是用三段的形式来表现的。三段诗作为彝族诗歌中一种独具魅力的体裁,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活跃在彝族社会的舞台。
作为彝族诗歌的精华部分,三段诗有一套严格的创作规律。最早提出三段诗这一概念的是著名的大诗文论及女诗人阿买妮,她在《彝语诗律论》中说:“三段诗一首,有的却说成,一首诗三段,如照他们说,一切诗当中,声韵不须讲,叙事就行了,如此三段诗,三段全叙事,那算什么诗”。(12)在这里,阿买妮明白地告诉我们“三段诗”和“诗三段”的区别。三段诗是有独特的艺术特征的,并非所有分为三段的诗歌就是“三段诗”。三段诗要成其为三段诗,必须具备其成立的条件:第一必须是三段;第二必须符合三段诗的基本规律,如声韵,格律等等。那么,三段诗有写什么特点呢?
首先,写人与写物相结合。阿买妮说:“写诗的时候,须分为三段,前两段写物,后一段点人,必须这样写”(13),“诗中的三段,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人”(14)。在这里,阿买妮为我们定下了写作三段诗的基本要求,明确三段诗“前两段写物,后一段点人,”或“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人”。布麦阿纽也说:“彝诗分三段,头段谈物体,二段指物身,三段是主骨”(15)从两位诗论家的诗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三段诗的一个特征就是“前两段写物,后一段写人”。因此,写物与写人相结合是彝族三段诗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比类与点题相结合。阿买妮说:“景物主相连,三段紧相依,段段声相扣,各段扣分明”(16)。布麦阿纽也说:“因为所有诗,都可分三段,三段三主体,主体旨可分,前两段为比,后一段点题,贵在前段起,主落于后段,中段为三连”(17)。后来的许多诗论家都赞同这一观点,都把比类与点题相结合的三段诗作为典范。
再次,三段诗具有独特的韵律。如前所述,阿买妮论述了三段诗的扣 押 连等韵律。布塔厄筹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古时三段诗,一段押一段,一段扣一段,押韵要分明,扣来不错乱”。(18)举娄布佗也说:“所有三段诗,一句一句押,一句一句明”。(19)实乍苦木也说:“每一种诗体,写法有定规,头段押二段,二段押三段,三段诗当中,互相都要押,互相都要扣,扣来才分明,扣来才有韵。”(20)由此看来,三段诗必须讲究押 扣 连等严格的韵律,才能构成完整的三段诗。
第四、三段诗字数必须相等,一般为五言。
综上所述,三段诗作为彝族诗歌的精华部分和主体部分,必然是具有独特特征的,对于它的规范的体例,不是只言片语能说清的,现举一首阿买妮著名的三段诗《花美啊花香》:
花美啊花香
春来百花香
花好春常在
冬来花不香
凉水啊凉水
春来好凉水
春天你不凉
冬天变雪水
姑娘啊姑娘
二十该当娘
二十不出嫁
年老难当娘
这首诗是彝族三段诗的典型范例,概括了所有三段诗所需要的格式 韵律以及主旨等等,成为了后世诗论家们常引的例子。
五、 彝族诗歌的格律
彝族诗歌从起源到成熟,都在不断的变革和创新,它不只在体例上变化,而且在格律上也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最终才形成自身独特的体系。
(一)、句式
彝族诗歌的主体部分是五言三段诗,因此,在形式上,除了“五言”和“三段”这两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外,在句式上是没有限制的。在整个彝族诗歌中,有短至两句 三句,长至四句 五句到几十句 上百句乃至几百句 甚至上千句。例如《漏卧鲁沟的婚礼》 《可乐古城传奇》 《阿诗玛》等叙事长诗。
(二)、韵律
具有完整体系的彝族诗歌,不管是较短的三段诗,还是较长的叙事长诗,都必须全面地遵循所有的彝诗格律规范。这些格律有两部分,一是形式方面,包括声 韵 调 字 连 扣 偶;二是内涵方面,包括根 主 骨 影 魂 风 味等。在这些格律要求中,形式方面的的韵和扣,特别是扣,它“是彝族诗歌区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关键性格律概念”,(21)它的格律功能在整个形式方面起主导作用,可以涵盖其它的格律功能,相当于汉诗的诗眼。而在内涵方面重要的概念是根 主 魂,特别是根,它是作为一首诗的内涵的核心而出现的,所以彝谚说:“写诗无根底,不算好诗章”。
六、 彝族诗歌的艺术特色
彝族是一个善于用物喻人的民族,在彝族诗歌中,无论是文人创作的,还是民间传唱的,都体现出汉诗《诗经》中具有的赋比兴艺术特色,赋多用于叙事长诗中,而比兴则多在较短的三段诗中得到体现和运用。
(一)、赋
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22)换句话说,赋就是叙述和描写。它是彝族诗歌中常用的一中表现手法。赋在彝族诗歌中形式多样,有的用于叙事赋,有的用于抒情赋,有的用于人生哲理赋,大量运用赋的修辞手法构成了一部部气势磅礴的叙事长诗。如《妈妈的女儿》 《一双彩虹》 《放鹅娄记》《漏卧鲁沟的婚礼》《红白杜鹃花》《金歌银歌》《撒俄述麦汝》《彩云情》《阿诗玛》,以及至今仍在民间传唱不衰的一系列“阿卖克”(出嫁歌) “曲谷”(情歌)
(二)、比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23),比,通俗的说法就是比喻,这是彝族诗歌中大量运用的修辞手法,特别在三段诗部分随处可见,可以说所有彝族诗歌都采用。例如流传于黔西北彝族地区的情歌《月明的三月》(本人译):
月明的三月
别点灯走路
若点灯走路
月亮会伤情
菜花开三月
别背箩讨菜
若背箩讨菜
菜花会伤情
情妹玩三月
情哥别出门
情哥若出门
情妹会伤情
这是一首严格的三段诗,它的比的用法是“段间比”,用前两段中的“明月” “菜花”来比喻后一段中的“情妹”,又同时用“点灯走路,月亮伤情;背箩讨菜,菜花伤情”来比喻“情哥出门,情妹伤情”,从而达到比的效果。又如《金歌银歌》中:“到了那时候,云来接太阳,不是接太阳,是哥来接妹;云来接月亮,不是接月亮,是哥来接妹,月娥阿姐青”(24)。这里运用的比是典型的范例,用自然之物“太阳,月亮,云彩”来比喻初恋中的男女,自然贴切,易于接受。
(三)、兴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25),说明白一点,兴就是借一个别的事物来开头,然后再转入正题的修辞表现手法.在彝族诗歌中比比皆是,兴的用法也与古代诗文论家提倡的三段诗的写法暗合,即“前两段写物,后一段点题”。例如流传于黔西北彝族地区的"阿卖克"(出嫁歌)<<飘啊飘啊飘>>(本人译):
飘啊飘啊飘
雪花飘啊飘
是谁送她去
太阳送她去
太阳回来了
雪花回不来
可怜啊可怜
雪花真可怜
飘啊飘啊飘
树叶飘啊飘
是谁送她去
风儿送她去
风儿回来了
树叶回不来
可怜啊可怜
树叶真可怜
飘啊飘啊飘
女儿飘啊飘
是谁送她去
媒人送她去
媒人回来了
女儿回不来
可怜真可怜
女儿真可怜
这首诗先说雪花飘去,树叶飘落,由此引出女儿出嫁,唱来伤情万分,真切感人,催人泪下,表达了女儿出嫁时与家人那种难分难舍之情。
七 、彝族诗歌的“以诗论诗”
作为用诗思维和创作的民族,诗的灵性注入了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具有独创性的诗论,即以诗论诗。在现今所收集到的彝族古代文论中,全部都是采用“以诗论诗”这种独特形式的。如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纽的《论彝诗体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佚名的《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这些诗论内容丰富多样,五彩缤纷,触及了彝族诗歌的方方面面,深入剖析了彝族诗歌的内涵.在诗论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创作要求的影响,这些诗论也讲究一定的的格律,从而其本身也构成了一首首庞大而精美的诗歌,堪称彝族诗论诗歌的佳作。
八、 彝族诗歌的影响
彝族诗歌从产生 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人常 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夷人大中曰昆,小重曰叟......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据考,当时南中是以彝族为主体的,而彝族又有自己古老的文字,并且好譬喻物的形式也同彝族诗歌的主旨要求相同。因此,“夷经”当指彝文典籍。可以看出,当时彝族诗歌已对其他民族有所影响。而在彝族内部,“五言三段诗‘成为稳定的体例。虽然这种体例对彝族诗歌多样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却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色。同时,她对彝族民间歌谣的规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深深影响了近现代彝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如吉狄马加,阿苏越尔,阿库乌雾,阿卓玛玮,奥吉戈卡,鲁弘阿立 ,阿诺阿布,他们的诗歌形式虽变,内涵却深深打上了彝族文化的烙印,“诗骨”仍是“彝根”。
九、 结束语
彝族是用诗思维和创作的民族,彝族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是祖国文学中的一枝奇葩.她博大精深,丰富灿烂,蕴涵了彝民族深刻的思想,堪称西南民族文学中的一绝。笔者生长在贵州乌蒙彝区,这里彝族文化保存完好,有众多的彝文古籍,彝族风情浓郁,自幼听着彝歌出门,唱着彝歌长大.因此对彝族文化特别是彝族诗歌情有独钟。彝族诗歌早也不是深院闺秀,但她终究没有被太多的人所认识。笔者试从几个方面对彝族诗歌作一些粗浅的介绍,以此让自己一心向往彝族诗学的心灵得以微薄的慰藉!
十 参考书目及注释
(1) (2):《彝族创世志.艺文志》16页 29--3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73--374页,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王明贵<<彝族三段诗研究>>8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6):毕摩:彝族知识分子,兼任神职.
(78910):漏侯布哲《谈诗说文》《彝族古代文论》345--346页,康健 王子尧 王治新 何积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131416):阿买妮《彝语诗律论》《彝族古代文论》66页 80页,康健 王子尧 王治新 何积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1517): 布麦阿纽《论彝诗体例》《彝族古代文论》187--188页,161页,202页,康健 王子
尧 王治新 何积全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布塔厄筹《论诗的写作》《彝族古代文论》102页,康健 王子尧 王治新 何积全编贵州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举娄布佗《诗歌写作谈》《彝族古代文论》121页,康健 王子尧 王治新 何积全编贵州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实乍苦木《彝诗九体论》《彝族古代文论》138页,康健 王子尧 王治新 何积全编贵州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王明贵《虎尾捉风》147页,华艺出版社2000版.
(24):王成有《彝族文学<金歌银歌>及其艺术特征》原载《红河民族研究》1993年刊.
(222325):朱熹
 该贴已经同步到 思想谱写辉煌的微博 该贴已经同步到 思想谱写辉煌的微博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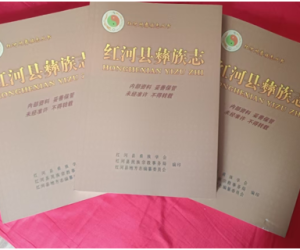 “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 《红河县彝28 人气# 彝学动态
“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 《红河县彝28 人气# 彝学动态 乌蒙村秀:千年彝裳绣出彝族文化指尖记忆37 人气#行摄彝乡
乌蒙村秀:千年彝裳绣出彝族文化指尖记忆37 人气#行摄彝乡 恳合呗:延续千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85 人气#历史文化
恳合呗:延续千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85 人气#历史文化 学彝文:每日一句谚语굈갱광꽄굈눔134 人气# 语言文字
学彝文:每日一句谚语굈갱광꽄굈눔134 人气# 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