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守望“撮泰吉”
毕节日报记者/陈燕南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为绵赓不绝的千秋后代誉满寰宇的非物质遗产。其中,彝族瑰丽多姿的传统文化遗产,在偏僻落后的村寨里默默地发展,流传,如彝族祖先的灵魂,神秘戏剧——撮泰吉,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有一个叫裸戛的小村寨。那里偏远,贫穷,交通不便,有一番陶渊明笔下那种与世隔绝的境界。然而,因为“撮泰吉”原始的名间艺术文化,让世人知道了这个小村寨。
“撮泰吉”在名间神秘地演奏村民对心灵深处的那份守望,把流传千百余年的“撮泰吉”融纳到原始自然宗教遗绪,用一种吟唱、舞姿、面具、装扮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体现了远古时代彝族祖先对神灵的崇拜。据说,在每当“撮泰吉”搬演时,人们都会迷失在这迷幻的戏剧艺术中,感到了一种中介性的力量将他们同那个不可捉摸的世界联系起来,同时,还感到一种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从而使个体生命融入到更大的生命之中的力量。为此,我有着强烈的欲望想去了解和挖掘。作为彝人的后代子孙,我热血沸腾的血脉里总有着那么一点眷恋和向往。
大一结束的暑假,我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在大学生彝学研究社社长李邦龙的带队下,我们乘上了去那块神秘国土威宁的巴车。一路磅礴的山势和那原野上的荞麦,牵着我的灵魂,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融入裸戛村这牵动人心的,具有民族代表意义的原始戏剧——撮泰吉。在板底乡经小学罗德慧老师,王平老师等其他有关民族研究人员介绍中,我们知道了“撮泰吉”的来历,流传习俗,表演过程和简介等有关内容:传说,在远古时候,有一年阴历六月天降大雪。庄稼全被冻死,人也死了大半,连播种的种子也没有了,人们正绝望之时,天神派“撮泰阿摩”(也就是彝族祖先的灵魂)送来种子,还帮助人们耕种,恢复了生产,解救了人们。灾难过后人们获得了丰收。后来,只要年景不好或天灾人祸,彝族人民便在阴历正月初三到十五夜晚化装成撮泰老人,扮演撮泰吉,以此驱除邢魔,祈愿风调雨顺,振作受挫的信心。因此,撮泰吉就这样产生于民间,默默不闻地在那深山野林中自生自长,保留了浓厚的原始艺术本色。
撮泰吉在名间有只传男不传女的习俗,如此,这种古老的戏剧在我国已经及其罕见,许多地区已经流失,没有了踪影。即使在威宁县板底乡的裸戛村,会跳的人也已经不多。如果这种传统的思想未能得到改变,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文化“撮泰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渐渐消失,所蕴藏的历史文化长廊也会逐渐随着消失。
撮泰吉在彝语中,被翻译为“人类刚刚变成的时代”或“人类变换的游戏”,反映的是变成鬼神的祖先当初迁徒,垦荒的艰难场面,并借助祖先的威灵来保佑后裔和驱逐邪魔瘟疫。因此也把撮泰吉理解为“请变成鬼神的老祖宗来保佑后裔的游戏”或“人变鬼神的游戏”。撮泰吉一般由10至17人扮演。主要人物是:惹戛阿布、阿布摩、阿达姆、阿安、麻洪摩、黑布等等,剧情从第一部的祭祀一直到第四部的扫寨,需要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结束。经过他们几个小时的讲述,让我在记忆深处隐隐约约摸索到了什么——小时候在板底乡赛马场上看过的唯一一次“撮泰吉”表演。回想那场景,还能让我迷幻于那古老的人类社会,那种在彝族祖先尚不会直立行走时发出的低沉的猿猴的叫声,那种面对困境无能为力,大喊“惹嘎阿布”向神求救的呼叫声;以及那种沉重的叙述彝族祖先迁徙过程的声音,那种在粮食丰收时欢乐的声音……
由于时间和天气关系,在板底住宿了两天,第三天早晨我们不得不返回威宁县城。在车上我忍不住想看看我们来回走过的这一片土地。望向窗外,道路旁原野上开满了红红绿绿的甜荞苦荞花,将彝乡大地装扮得好似一幅幅锦绣般的毯子。东风吹过,带来了彝乡浓浓的待客气息和那种原始的民间艺术,身体和精神的进化与升华,彝族人民心灵对神的守望的空气。
|
 有进展: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协作推进彝族古文8 人气# 彝学动态
有进展: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协作推进彝族古文8 人气# 彝学动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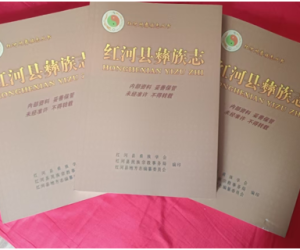 “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 《红河县彝97 人气# 彝学动态
“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 《红河县彝97 人气# 彝学动态 乌蒙村秀:千年彝裳绣出彝族文化指尖记忆111 人气#行摄彝乡
乌蒙村秀:千年彝裳绣出彝族文化指尖记忆111 人气#行摄彝乡 恳合呗:延续千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51 人气#历史文化
恳合呗:延续千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51 人气#历史文化 /1
/1 